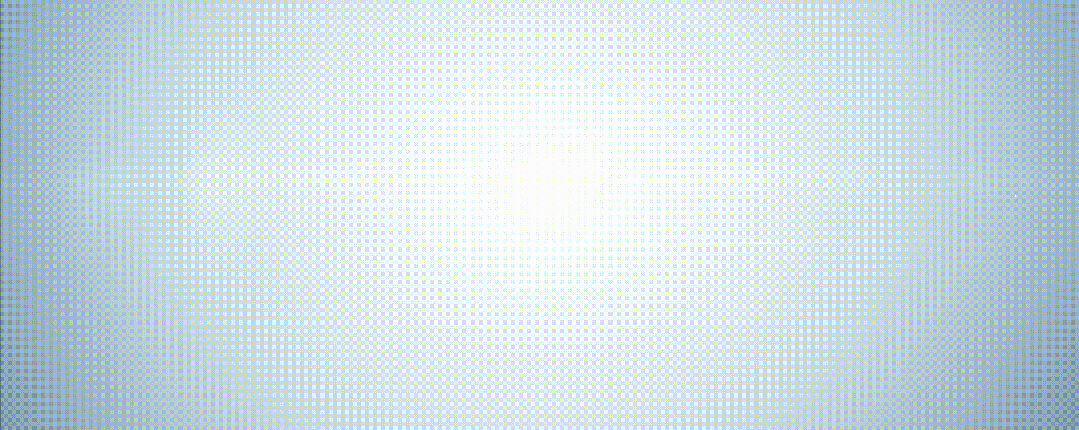

翻开今天的日历,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“立秋”二字,总嫌时间过得很慢,可是转眼已到秋天,今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,在立秋的清晨,天边还残留着几片薄纱般的云霞,阳光已不再似盛夏那般炽烈,而是裹着一层淡淡的金边,轻柔地洒在飘窗上。我推开窗,一缕微风拂过面颊,带着微凉的湿润,伴随着昨晚雨后的清新,仿佛秋天在耳畔轻声打了个招呼。这便是立秋了,暑气未褪,秋意已悄然蛰伏在光阴的褶皱里。

记忆中的立秋总与奶奶的手艺相关,小时候,每到这个时节,菜园里剩下的最后一茬西瓜,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,西瓜表皮已褪去青翠,染上一层淡黄,像被岁月镀了层薄金,她将西瓜切成月牙状的小块,摆在竹编的圆盘里,招呼我们围坐在门口的石榴树下。刀刃切开瓜皮时发出的清脆声响,汁水顺着纹路流淌的簌簌声,混着蝉鸣的余韵,成了童年立秋特有的韵律。奶奶常说:“立秋吃西瓜,能咬住夏天的尾巴,也能尝到秋天的头茬甜。”我们啃着瓜瓣,舌尖残留着最后的盛夏甘甜,却不知晓,那些被我们随手丢弃的瓜籽,已在泥土里悄然酝酿着下一个轮回的生命。西瓜是奶奶对抗酷暑的智慧,更是她对季节流转的敬畏与顺应。
午后,阳光变得慵懒起来,调皮的我们在池塘边的坝梗上玩耍,池塘中的芦苇丛已褪去碧色,穗尖泛出微黄,风掠过时,摇曳生姿,宛如一群身着淡黄纱裙的舞者。河水依然清澈,在池塘中嬉戏了一个夏天的喧闹在这一刻安静下来,偶尔几只白鹭掠过水面,翅尖点起涟漪,倒映着天空渐深的蓝。池塘两岸的农人弯腰收割稻穗,镰刀与秸秆相触的嚓嚓声传来,清脆而富有节奏,像是大地在谱写秋的序曲。远处,炊烟袅袅升起,与暮色融为一体,立秋,既是告别,亦是新生。
暮色渐浓时,疯玩了一下午的我回到家中,母亲在灶台上炖起了排骨汤。锅里的热气氤氲着整个厨房,排骨与莲藕在沸水中翻滚,溢出阵阵暖香。这是“贴秋膘”的老习俗,母亲总说,秋风起时,要补些营养,才能抵御渐寒的天气。喝上一碗排骨汤,咬着煮的软软糯糯的莲藕,满足的欣喜在脸上慢慢晕染开,在立秋的烟火气里模糊而清晰起来,让人懂得,那些被岁月沉淀的情感,恰似秋酿的酒,愈久愈醇厚。
夜色终于浸透了天空,我坐在天井边,仰望繁星初现。北斗七星已悄然偏移了方位,银河斜斜地流淌,仿佛在指引季节的迁徙。秋虫开始低吟,声调不再如夏夜那般急促,而是舒缓绵长,像在诉说一段悠远的往事。

立秋,是节气更迭中的一枚书签,夹在夏与冬的扉页间。它教会我们在炽热与清冷之间,寻得一份从容的过渡;在繁华与萧瑟的交替里,品出一缕淡然的况味。那些被岁月镌刻在立秋里的往事,如同秋叶上斑驳的纹路,每一道褶皱,都藏着光阴的故事。此刻,我听见季节在耳畔低语:且让盛夏的繁华沉淀为秋的底蕴,待凉风拂过,自有另一番丰盈在枝头静候。
立秋,原不必是风起叶落的壮阔,也未必是寒意袭人的预告。它只是天地间一个微妙的转折点,是暑热中悄然渗入的一丝凉意,是池塘坝梗上微卷的芦苇叶,是雾气腾腾的一碗莲藕炖排骨莲蓬,是奶奶那盘切得整齐的西瓜沉淀的岁月温情。
立秋了。秋,正在路上。正如古人所感:“云天收夏色,木叶动秋声。”这“动”字,是萌动,是初醒,是生命在季节的琴弦上,奏响下一个乐章的序曲。

文:李晶
图片:由AI生成
编辑:杨洪梅
审核:廖洪波